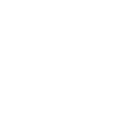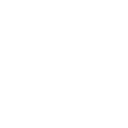金沙娱乐,金沙娱乐城官网,金沙娱乐城app,金沙娱乐城,金沙赌场网站,金沙博彩,金沙集团官网,金沙赌场网站,威尼斯人赌场,太阳城,太阳城娱乐,太阳城app,太阳城app下载,太阳城集团,太阳城赌场,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太阳城集团官网,太阳城网站注册,太阳城注册网址,澳门赌场app,澳门赌场官网,澳门赌场在线

“现在展览难做!”这是策展人普遍的共识和感叹。策展人从追求理想、力所能及地持续实践,到希冀通过展览项目对艺术生态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与影响,如今已逐渐转变为小心翼翼的平衡和讨巧策略。各种展览看似此起彼伏,更多是在“温水煮青蛙”中,享受着一种自以为是的乐趣。国内的双年展、三年展等周期性大展,虽然题目髙蹈、经费不菲、宣传声势浩大,其实,来来就是那些有官僚身份和背书的策展人,以及早已看腻了的作品。观后无感,且如同鸡肋!
在我看来,周期性大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将策展理念转化为适宜的展览空间形态,以及如何让观众通过展览获得更多的批判性视角和启发。因为策展和展览本身,不是研究或论文式写作,而是需要在作品、空间与观众之间建立一种沟通和带入的关联与途径;需要在时代的幕间与转向中,寻求新的契合点,发现新问题,包括在地性、现场性、公共性、深入性等,从而摆脱和规避展览策划的简单化、嘉年华式的节庆以及商业、政绩、文旅的附庸。
在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时代,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种由现实导致的不确定性未来,尤其是政治与经济影响所造成的暂时难以逾越的边界、限制、阻隔等人为因素,使策展陷入了一种不安与焦虑之中。那么,如何根据中国和世界局势的新变化,策划具有明确文化针对性的主题性展览?如何建立所谓艺术中心与边缘、边地之间相互打破的有效途径?如何超越白盒子美术馆策展的固有方式?如何调整当代艺术进入乡镇的展览机制?这些正是中国当下流行的,甚至不断扩张的当代艺术周期性大展和不同程度地向乡镇、田野转向的现实问题。因此,反省、解决这种瓶颈的状态,突破以往的沉淀与寻求发展的途径共域,也就迫在眉睫了。
如果说在美术馆或其他展览空间策划展览,需要在夹缝中谨慎地适应现实环境,符合来自各方利益的诉求和规则限定,那么策展人在保持其价值观和基本立场态度的同时,既要从“在地”与“全球”的视角发声,不断超越流行的策展模式,还要在冠冕堂皇的表面下,暗藏问题意识的锋芒。同时,策展人不仅要面对主办方的行政管理机制和工作团队,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虽然有些策展理念和实施是可以把握的,但在操作层面上却难以控制,远比以往所经历、预设、想象的更为复杂和意外。特别是在展览项目的落实过程中,那些需要不断适应各种行政机制的细碎瞬间,额外制造了诸多焦虑、纠结和争执。
如今,我们似乎正身处一个不再热衷于谈论航海远方的时代。全球化的受阻和转向,地缘政治的分裂与文化冷战的加剧,导致了狭隘的保守、民族、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磨损着我们对远方的眺望。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使保守主义从边缘走向中心,不断造成的有限视距,加剧了人们的封闭与内卷,尤其是疫情的冲击以及眼下的贸易战,加倍地将我们置于封闭、疏离的境地。在内外双重制约与主体失衡的夹击下,当代艺术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之中。全球化曾经所具有的某种难以抗拒的魔力也在渐渐消退……艺术家们既不在此聚集,也不从此出发。在这种背景下如此发问,不仅是出于一种文化的自觉,也是策展人、艺术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我们都是躯壳里的生命,也是人生旅程中匆匆的赶路人,可能比以往更加敏感于时代浪潮的流向和水温的骤然转变。
当我们降临于世间,我们究竟是干什么来了?人生的种种困惑、迷茫、无力、混沌,只会随着时代的复杂指数不断加深,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充满了未知。以这一问题意识为线索,从提问到输出,我们寻求相互链接的去向、依托与归宿。又或者,在网生文化中的数字化生存、人工智能的AI时代呼啸而来之时,我们更需要对其进行迭代的思考与觉知,并试图在无去来处中寻找方向和未来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因此,这是一种以主动姿态去探索问题的策展方式,一种寻找人生意义、价值和责任的选择与表达。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远渡重洋抵达澳门,开启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遥想当年,他的到来或许在中国朝野内外引发了普遍的疑问:他干什么来了?回顾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的艰辛历程,我们发现他的出发点就是他的目的地。作为“西学东渐”的先驱,他从澳门起步,将西方科技知识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使其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在欧洲与中国之间铺就了一条可行的文化交流之路,促进了中西两大文明的对接、碰撞与融合,功不可没!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中写道:“在这片未知的地域,利玛窦已经走得太远,远超他预料。他有时茫然无着,不知自己是否应该返回,自己是否还能够返回。”
作为当代艺术创作,艺术家即便有创新的观念,最终仍需要通过作品的媒材利用、语言方式和视觉形态进行传递,使观众在面对作品时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信息。作为策展人,则需要根据每次展览的不同主题和展示空间,将参展作品巧妙地贯穿于有限的展览空间之中。这不仅要求策展人相对充分地满足每一位艺术家作品呈现的需求,还要考虑参展作品之间的逻辑和视觉关联,同时摆脱当前流行的以文本或图像编辑为主的展陈模式,构建具有一定超越性的多维、立体的视觉空间。这不仅是空间的形式设置,更是人与空间环境之间关系的载体。策展人更关注在空间所看到、听到、感知到的最佳视觉效果,这也是策展人在展览空间设置上的关键所在。
首先,我们突破了以往双年展惯常的、均质化的模式,即在一个主题框架下设立若干单元主题,通过梳理、汇集与主题和单元主题相关的艺术家作品。此次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主展场,我们将来自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十六位艺术家的八十件(组)作品,以日常生活的多样空间设置、命名和阐释,折叠出我们一起走过的生存旅途。这包括由外及里或由里及外的入口、宫殿、迷宫、广场、赌场、街区、里屋、出口、太空等二十个空间叙事。从而将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主场展作为全球化“在地性”的一个锚点、缩影和容器。
其次,我们将展览空间扩展到一些非展览的公共空间,如卫生间、通道、后窗等,并以夹角、空隙、域外等替代空间的命名,作为展示空间与零余空间之间的一种多功能开放空间的灵活处理与补充。这种由单元主题的分类、归纳向生活空间缝隙里的嵌套的转向,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一至三层的两千多平方米的展厅内,通过叠穿架屋的方式,穿插出多种不同空间。这是一种打破现有空间秩序的预兆,形成了参展作品的媒介与信息、屏幕与视线、影像与文本、观念与映射之间的暗流涌动。
展览作品的呈现往往需要与特定的展览空间相结合。我们特别委托“众建筑事务所”对展览进行了“全域空间”的设计。他们借鉴澳门街区标牌的样式,以立体的空间魔块,穿梭于紧凑的展览之中。这种设计既有曲面和硬边的冲撞,又有统一的格局,同时在不同状态和空间之间形成了过渡与聚合的“阈限”特征,由此构成了一种在空间视觉中连续互动的标识。这不仅是空间形式的堆叠,还掣肘于空间对抗的平衡。其作用不在于寻找作品的对应关系,而在于他们所规约的空间“聚合”中,借地而生,通过这些海内外艺术家的作品构成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观众可以在作品与空间的流动中驻足观赏,捕捉日常空间、展览空间与作品空间之间的漂浮和游离,感受澳门与世界的存在。
你在此生活或旅行,聚焦于空间环境与个体感知的交接地带,你的经历、故事便是这些空间命运的缩影和延续。每个角落都是过往生活的见证,也终将成为过去的痕迹、未来的走向。其目的在于将展览主题的诘问和展览本身,通过艺术家的创作融入日常空间的情境,再通过展示方式的空间介入,浮现特定的空间结构和叙事。其中,可能蕴含着极其特别的社会仪式的含义,也可能在新的展览条件下发生扭曲变形的象征。这一切最终构成了这次展览主题与空间设置的完整概念和意义。这是对双年展现状、问题和困境本身的一次考量。或许正是这次展览的空间命名和设置上的进与出,形成了与其他周期性大展的殊异之处。在今天看似驳杂但又略显同质的展览群像中,这也可以视为扩展与突破周期性大展在空间设置边界上的一次实验。
这种“一厢情愿”的尝试,直接牵涉到参展的新、旧作品的不同针对性指向,以及作品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如何根据展厅的条件,布展、搭建的可能性,以及预算限制等非常具体的因素前提下,既要结合我们有限的艺术家资源,又要考虑每一位艺术家作品的充分展示,将作品纳入我们的空间设置,并兼顾从入口到街区、广场……再到出口、太空的参观动线。这是一个在有限的展览空间中,将艺术家作品按照策展人命名的空间进行串联和重构的过程,如同在穿越复杂而不确定的空间语境中的现场博弈。也许不合时宜,也许难免牵强附会,但这恰是我们作为策展人有意设置障碍和跨越障碍的过程。倘若没有这些障碍,没有这些过程,也就没有跨越时的升华。设置和跨越障碍,克服倦怠,正是我们要做的事儿。这可以作为策展实验性的一种代偿,也是我们赖以生存与表达的工作方式之一。
除了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主场展之外,我们策展团队还负责本届双年展公共艺术展的策划。尽管主场展和公共艺术展在策展理念和场地上略有不同,但我们希望二者能形成一种既各自独立又互补互助的关系。具体而言,在主场展中,我们将四十六位艺术家的80件(组)作品,在二十个紧凑的空间中穿插呈现;那么在公共艺术展中,我们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空间,通过将八位主导艺术家的物件(组)作品置放在城市的社区之中,划分出一条澳门的在地性与全球化关系的线索,连接更为广泛的社群、居民及游客栖息的现场,以嵌入式的互动方式为澳门的在地文化赋予更广阔的空间叙事。
公共性具有公共空间的文化属性,它是由公共场所和公共媒介所构成的,公众可以自由进入、参与交往。公共性最本质的含义是对权力话语的解构和颠覆。因此,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并不意味着简单、生硬地将雕塑、装置等作品镶嵌到城市或社区的某个空间,或仅强调观众需仰视才得见的宣喻教化和审美功能。随着当代艺术的不断扩展,当公共艺术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时,需要面对社区、社群错综复杂的环境和关系,创作者或以“邻居”的身份融入其中。“相邻”意味着从艺术作品和现场的具体条件出发,也意味着策展人需要身在其中地去想象展览,尤其需要艺术家转换角度去重新思考公共艺术创作的动机和工作内容。
公众既是公共空间的介入者,又是保持有限距离的观察者。当公共空间的生产力夯实在澳门城市的地表和岩层之上,就形成了一种参与和互动所赋予的视觉感受和无形的能量。观众在此空间移步,探索自我与他人的联系,从而理解人与空间的交互模式。公共艺术这种从物化形态到行动介入的多重转向,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平等对待、尊重和开放,既消弭了艺术家及作品与公众之间的隔阂,又构成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生动“在场”体验,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艺术改变生活的有效性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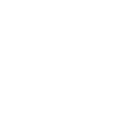

020-88888888